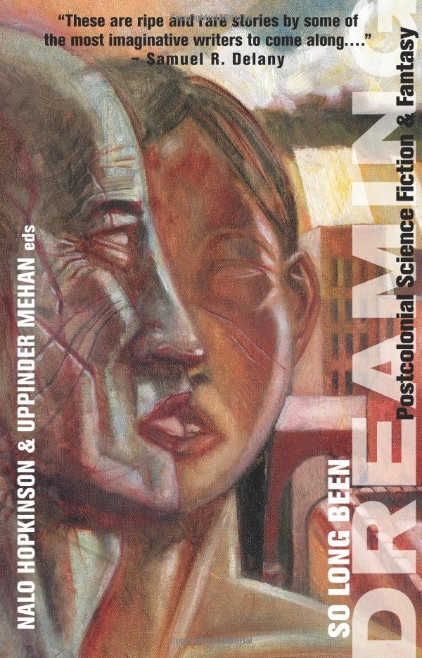行星马克思

欢迎登陆行星马克思
行星马克思
时间:2019
作者:长征计划

读书会 #1:地球如何成为一台传感器?
行星马克思
时间:2019年3月21日
地点:长征空间,北京
嘉宾:赵要、王翊加

读书会 #2:土酷土产土生梦
行星马克思
时间:2019年4月20日
地点:泰康空间,北京
嘉宾:毛晨雨、向在荣

读书会 #3:脏化学
行星马克思
时间:2019年5月18日
地点: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北京
嘉宾:魏颖、刘张铂泷

读书会 #5:破生产链
行星马克思
时间:2019年6月22日
地点:金杜艺术中心,北京
嘉宾:刘韡、宋轶

读书会 #6:宇宙空调
行星马克思
时间:2019年8月3日
地点:706青年空间,北京
主讲人:翁佳

读书会#7:脱媒体
行星马克思
时间:2019年8月24日
地点:民生现代美术馆,北京
主持/主讲:许大小

读书会#8:后历史魔法
行星马克思
时间:2019年9月21日
地点:长征空间,北京
主讲人:徐瑞钰

读书会#9:如何做一台科技的祛魅手术?
行星马克思
时间:2019年11月10日
地点:McaM明当代美术馆,上海
嘉宾:林丽纯(心灵途径)、龙星如(阅读途径)

长征计划:赤字团
行星马克思
时间:2019年11月2日 至 2020年1月8日
地点:长征空间,北京
艺术家:陈滢如、林丽纯、张欣、阿拉差·楚利恭、冯火、亚洲酒店项目与佐佐木玄+宫川敬一、金雅瑛、小泉明郎、李继忠、李泳翔、梁硕、长征集体、毛晨雨、行星马克思、覃小诗、李山+赵天汲(社会敏感性研发部)、丘阿明、陶辉、童义欣、王拓、西亚蝶
欢迎登陆行星马克思
行星马克思
时间:2019
作者:长征计划
技术哲学家于光远在1996年进行了题名为“地球之小和地球之大——提出一个有关21世纪建设的大思路” 的发言。这个带有官方性质的论述,指出一条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运用为趋势规划的方法。在这一则辩证法描绘的双重地球形象中,地球是人类存在的条件,也是技术圈所覆盖的身体。这个形象本身的复杂性在于:保护和发展并行。为了试图摆脱这则由哲学所推导出来的技术乐观论,长征计划以“行星马克思”的形象为题,发起以读本贴吧及系列读书会为形式的研究项目。“行星马克思”项目旨在从历史的文本中找到回应今日科技所带来的文化以及认识论危机。其中的假设就是:在过去面对星球规模的变动时刻中,包括科幻文学、民族人类学、文学批评在内的思想家,总是试着重新寻找我们与自然、生态、土生和科技的关系,并提出新的视野尝试适应这种改变所带来的危机。为了持续观察与此相关的许多艺术项目参照各自特地线索而发展出来的思考和实践,长征计划提议建立一组开放的读本贴吧。项目邀请进行中的展览研究项目各自提出在科技、自然、土生、民族等范畴之间交集地带的文本。这些文本将透过协作制作成一系列跨展览的工作读本。我们希望以此鼓励艺术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并进一步演化出一个有机的沟通网络。
什么是“行星马克思”?
“行星马克思”由线上及线下两部分组成:基于Facebook小组的线上读本贴吧以及系列线下主题读书会系列。线上读本贴吧旨在收集各类文本,集结为一个公开的读本数据库;而线下读书会则根据每期主题由线上读本库选取的材料出发,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比对和深化,旨在生成新的话语探讨,最终反馈至线上读本贴吧。项目欢迎正在进行中的各种关于科技、自然、土生、民族的研究项目提出各自的工作读本,它们最终将多个不同项目聚集的智慧集结起来,作为一个共享读本库以及相互交流参照的基础。
“行星马克思”从哪些文本出发?
彼得·克鲁泡特金(俄国,1842-1921)
《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引言,1902
节选自:克鲁泡特金,“引言”,《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是一位地理学家,制图学家,生活中他也是位园艺爱好者。在达尔文主义的论述席卷欧洲的情况下,他实际到西伯利亚和满洲考察的经历引发了他撰写《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的动机。对他而言,物种在资源稀少而竞争激烈的情况中,不可能有任何演化的余裕,另一方面,物种在冰天雪地中只有互助才能适应环境。这个片段为我们提供了左翼论述以及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少见的生态线索。如果说今天达尔文主义的物种竞争论仍旧以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的黑暗森林理论流行于文化圈中,那么,在这种泛民族主义的无意识中,重新思考启蒙/革命、辩证/演化的历史关系,有助于我们想象不同于物竞天择的主体存有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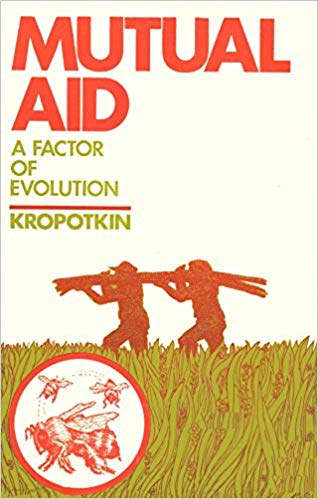
于光远(中国,1915-2013)
“地球之小”和“地球之大”——提出一个有关二十一世纪建设的大思路,1996
节选自:于光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南昌:江西科学技术,1996
在邓小平的政策智库中,鼓吹自然辩证法的技术哲学家于光远在1996年以地球之小和地球之大的说法,形象化了“技术圈”意识,也反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态观。就今天的视角而言,也许这种从革命到生命政治的转向,可以说是加州意识形态的颠倒版本。另一方面, 谈“自然的人化”,并认为人以及自然仅仅是资源,其生态观无疑是自然主义式的,但这种自然观确实仍是目前中国的主流叙述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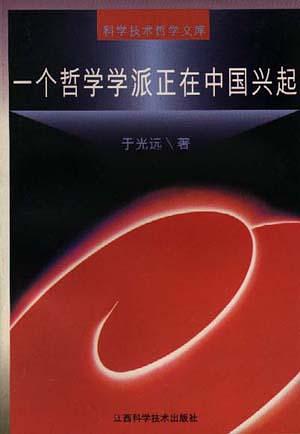
李泽厚与刘再复(中国,1930-;1941-)
关于物质一元与精神多元,1995
节选自:李泽厚与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1995
李泽厚在80年代极具影响力的论述在于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启蒙与革命相互竞逐的复杂性。以知识论为原则的启蒙,从五四、鲁迅传统而生,到80年代激起一次回潮。救亡的话语在40年代的民族形式、60年代的喜闻乐见、大众艺术,至今天的中国科幻民族主义都见得到它的踪迹。而他与刘再复于90年代以对话形式所激起的“告别革命”大讨论背后,则隐藏一则没有这么多人谈论的议题: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思考演化及改良的方案,并且散见于他们描述“精神生态”及“多元共生”等议程中。

童恩正(中国,1935-1997)
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1989
节选自:童恩正,“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人民,1989
作为50年代开始科幻写作的前行者,小说家童恩正引领着改革开放初期的科幻热。其科幻小说倡导科学文艺也要有民族形式。因此在其小说中,即将到来的时间往往也涉及远古。而他同时也是位改革开放时期重要的人类学家。在其《文化人类学》中,他透过这个学科的研究思考技术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类困境的解套方式“不能光靠科学和技术的新发展”而是需要新的认识论,以及思考“人与自然的适应关系”。也许,好的科幻小说的标准也许是:小说如何提出人适应自然,以及民族如何适应科学这样的具体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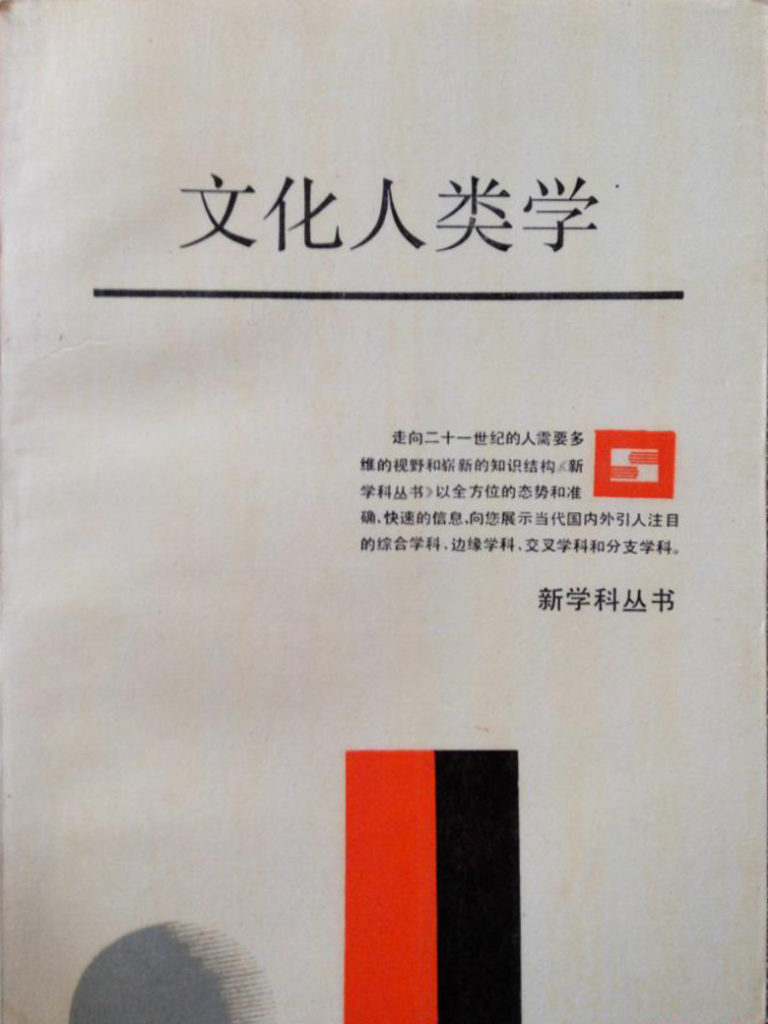
阿米塔夫·高希(印度,1956-)
气候与科幻,2016
节选自:Amitav Ghosh, The Great Derangemen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nthinkable, Berlin: Berlin Family Lectures, 2016
印度小说家阿米塔夫·高希思考生态的方式并非将它发展成一个文类。在他的非虚构写作《大错乱:气候变化与无法想像之事》里,高希抱持着“气候危机其实是文化危机,以及想象力的危机”的观点。气候的状况其实一直都是所有文学作品中无所不在的背景,而我们所要做的,便是重新想象这些背景如何塑造了我们欲望的指向。在选文中,高希描绘1815年,历史上最大的火山爆发造成的冷天及阴雨如何成为玛丽·雪莱在当年撰写《科学怪人》那奇诡氛围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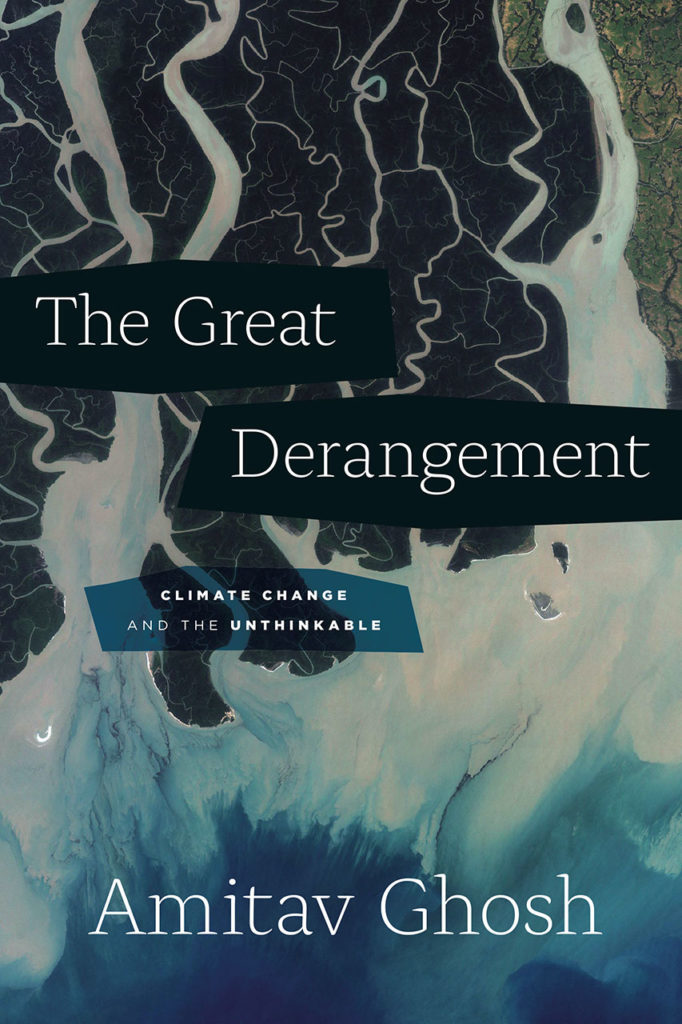
娜洛·霍普金森(牙买加,1960-)
主人的工具,2004
节选自:Nalo Hopkinson and Uppinder Mehan eds, So Long Been Dreaming: Postcolonial Science Fiction & Fantasy, Vancouver: Arsenal Pulp Press, 2004
娜洛·霍普金森在其为共同编辑的后殖民科幻小说集所作的序言中简明概括了科幻文类背后的双螺旋结构。科幻写作作为“主人的工具”,使用它意味着“冒着内化自身被殖民性的风险在写作”。譬如说,科幻背后带有的殖民理性体现在:古典科幻中的拓殖想象,对边缘的多数而言其实是非虚构的历史化现实。霍普金森同时指出,一个好的科幻小说家应当调解这种看似有害的经验,并尽其所能在描写科技演化的形态上使用非西方的文学隐喻。